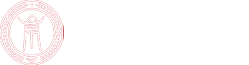中国与日本交流的早期横跨日本的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
历史需要见微知著,服饰交流看似在整个文化艺术的交流中无足轻重,但服饰交流伴随着民族大变迁和社会的剧烈变革。中日之间的交流史从汉唐开始一直绵延至今,两位一衣带水的近邻在文化,艺术的发展上透过小小服饰交流产生了一些思想的碰撞与解放,本文将从古代时期各个朝代的中日交流为基础,浅析中日之间服饰交流的变迁与其背后的深意。
一、早期的中日服饰交流
最早的中日之间的服饰交流起源于朝贡。中日之间最早的交流记录见于《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朝贡之时,礼物互赠,由于当时日本生产力低下,仅能以“生口”为礼,然而此时,中国已是统一的大国,所赠予的礼物代表了当时国家最先进的生产力,且在所赠礼物中以织物珠宝为最。这一种朝贡关系从西汉直到唐朝,在这段时间内中日由于生产力不平等,文化服饰发展水平不一,故此时的服饰交流以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入为主。
1.弥生时期服饰技术交流情况
中国与日本交流的早期横跨日本的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两大时代,中日之间交流也从刚开始的稀疏发展到频繁,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逐渐辐射到两国的各个方方面面,服饰交流便是因此而兴起。
日本的弥生时代大致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后半叶。在弥生时代早期,日本服饰主要以树皮根茎为原料,仅能以原始的平织法制作稀疏的麻布,《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记载了弥生时期倭人的服装样式,即“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和“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服饰文化的落后,穿着没有太多缝补,直接将整块布罩在身上。
日本在与中国的朝贡中逐渐吸收了中国的纺织技术,通过学习掀起了属于他们的服饰革命。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魏明帝景初二年以后的10年间,倭女王国派到中国的使者多达4次,这四次来访记录中可以一窥那时中国与日本服饰交流的情况。景初二年倭女王卑弥呼献给魏国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两匹两丈。而魏明帝回赠礼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粟罽10张,蒨绛50匹,绀青50匹。
另又特赠绀地句文锦3匹,细斑华罽5张,白绢50匹…… 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50斤,到了正始四年,倭女王提供了相比于上次朝贡更为丰富的纺织品,献给魏国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从斑布到锦帛中日习俗文化比较,日本的服饰只经过了短短5年,便已发生了质变。到了弥生时代晚期,日本的纺织品已经相当丰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也有“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的记载,可见日本的服饰种类相当发达。
在弥生时代的中日服饰的交流中,除了两国之间互相朝贡往来交流外,归化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所谓归化人,即来自日本列岛以外的人,归化人中主要以朝鲜人和汉族人居多,归化的汉族人大多从事各种技艺工种。在《日本书纪》中记载道:“十四年春二月,百济王贡缝衣工女,曰真毛津,是今来目衣缝之始祖也。是岁,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从中可以得知当时归化的规模和人数十分巨大,给日本当时的服饰文化也带来了冲击。
弥生时期日本服饰文化受大陆影响,发生了几点新的变化:一是象征着原始部落文化的诸如骨、角、牙等装饰品逐渐消失,中国所制造的各类装饰成为权贵百姓们追捧的潮流。这些都可以从弥生时期所出土的文物,如铜镜,璧,青铜鉴这些带有明显中国服饰文化风格的物品可见;二是弥生时代日本的服饰制作呈现出分工化趋势。由于服饰文化的丰富,一件服饰的制作变得繁琐,已不是一家就能完成,需要多家分工合作才能做成一件华服。
2.古坟时期中日服饰交流情况
经过了弥生时期的初步交流与发展中日习俗文化比较,当时间来到古坟时期时,中日服饰文化交流来到了一个高峰期。此时交流形式仍是主要以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出为主。古坟时期中日的交流往来十分频繁,包含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在服饰交流的领域主要体现在日本对中国纺织和服装制作技术的学习交流上。
《日本书纪》中记载道:“遣阿直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在这一时期,倭王除了接受各类织物赠礼外,开始主动跟官方要求擅长“汉织”、“吴织”的技术人员来日本发展,用高报酬和高地位吸引中国纺织人才归化于日本,以至于倭王专门为来日的“吴织”技术工人们修路建房,赐给一块土地来安置,并命名为“吴原”,将这些工人们奉为大三轮大神。这些中国纺织工匠将技术带给日本人民,日本以这些纺织技术为基础,也发展了后来的飞鸟衣缝部和伊势衣缝部。

相比于弥生时期的追捧大陆服饰品,到了古坟时期,这种模仿与追捧也到了一个高潮。根据出土的文物壁画可以得知,此时日本服饰与汉,韩服饰的相同或相似的元素较多。古坟时期男子上衣下裤的样式与中国在北魏时期大力推广的胡服裤褶形式基本相同。而在饰品领域,古坟时期日本盛行饰品,有手饰、脚饰、颈饰,以及古坟后期出现的耳饰,这些饰品很多都是勾玉形状,以金、银、铜制之。这些饰品样式均与中国同时期饰品样式相似,有的来源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商朝。
二、中日服饰交流的盛况
经过弥生时期和古坟时期的中日服饰交流,此时两国间文化水平,纺织水平虽然仍存在差距,但是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天壤之别,中日之间的服饰交流也从刚开始的单向输入变成了相互学习。
1.隋唐时期中日服饰交流情况
隋唐时期,中国成为了地区内独一无二的强大帝国,有着万邦来朝的盛况。日本也是来朝的万国之一,此时官方间的朝贡交流虽然仍存在,大量的日本遣唐使得以在中国生活数十年,乃至于封唐官,入唐殿。遣唐使回国后大力宣扬唐文化,以至于日本对中国服饰的学习模仿达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状态,也由于此时中国对于外来文化风俗十分开放,所以在这个常年交流过程中,中国人也乐于吸纳新奇的异域服饰。唐朝时,日本正处于奈良时代,此时遣唐使积极在日本传播在华见闻,力主天皇实行服饰革新。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日本天皇在颁布《大宝律令》明文规定制作衣服要仿造中国样式,宫廷朝服也模仿唐朝朝服设计。此时中国的百姓衣着均为右襟,于是下令“天下百姓右襟”。在这场服饰革新中,日本对唐朝的学习有些矫枉过正,某种程度上约束了本民族的创新性。至于中国人对于日本特色服饰的喜爱,可以从李白的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中“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一句可见一斑,在本诗中李白自注到日本裘为著名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所赠,间接说明日本纺织品已成功在中国流通,受到部分唐人欢迎。
2.宋元明清时期中日服饰交流情况
经历了唐朝的交流盛世,来到宋元时期,中日交流情况发生了改变,官方交流显得没有民间的贸易交流频繁,商人成为此时中日服饰交流的主力军。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处于南北分治,而且元朝时蒙古族统一中国,与日本关系不佳,明清时与日关系继续恶化,所以此时官方交流基本上趋于消减,此时中日服饰交流仅靠民间贸易难以维系,直到清朝闭关锁国,两国间的交流基本废止。
于是中日服饰至此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日本保留唐制,结合民族特点发展,日本服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创新之路,逐渐发展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和服。而中国的服饰文化经历沧海浮沉,呈现出民族多样性,汉服不再是唯一的中国特色服饰,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开始出现,例如旗袍,就是属于融合满族特色的服饰。
三、总结
中日之间的服饰交流是两国关系和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通过中日之间的服饰交流史可以看出中日之间文化联系十分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对艺术,对美学的看法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虽然日本在服饰交流的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接受学习的角色,但是并没有因为学习和模仿而磨灭了自己民族服饰的独到之处,体现出日本大和民族强劲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交流过程中,中国很长时间也是处于老师的角色,辅导传授日本先进纺织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也体现了我中华泱泱大国的气度。
参考文献:
[1]马兴国. 中日服饰习俗交流初探
[2]竺小恩.古坟时代:中日服饰文化交流形成第一次高潮
[3]贾莉.古服之变——中日服饰近代化进程之比较
- 上一篇 6款年货白酒礼盒装,送礼不怕无人识了
- 下一篇 茅乡纯粮酒,好水出好酒